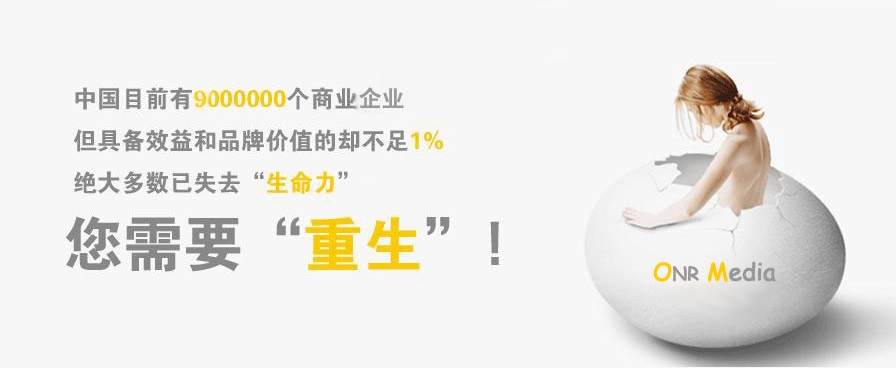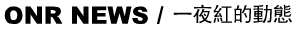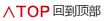畢贛導(dǎo)演的新片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還沒拍出來之前,就被不少西方電影類媒體評為2018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作品。終于,這部年度期待片,會在2018年最后一天和觀眾見面。
最初很多人好奇,一貫使用素人演員拍小成本電影的青年導(dǎo)演,獲得了資本的加持,又是否能夠駕馭紛繁復(fù)雜的電影工業(yè)及其背后的一切條條框框。而畢贛似乎依然保持了他的“精神領(lǐng)袖”風(fēng)范,讓片方心悅誠服“錢花得值”,讓演員們感嘆拍電影獲得難得的“享受”經(jīng)驗(yàn)。
他依然才華橫溢地用鏡頭寫詩,做詩意的夢。

畢贛喜歡用電影詮釋夢,也希望觀眾在看電影時能有做夢的感覺。上映之前,我們專訪了電影的主創(chuàng),從他們言語中,大概能夠拼湊出一些這個夢是怎么做出來的過程,以及他們自己“做夢”時的樣子。

螳螂:和山里的自然濕氣融為一體
畢贛和湯唯,雖然身上都貼著和“文藝片”有關(guān)的標(biāo)簽,但其實(shí)是截然不同的兩種“文藝”。很多人問起過合作的緣起,畢贛總說,因?yàn)閷憚”镜臅r候就浮現(xiàn)的湯唯的臉。再追問為什么浮現(xiàn)的會是這張臉,他說,“那你可能要把我的腦袋挖出來讓科學(xué)家去解剖看看。”
湯唯在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演的角色叫萬綺雯,上世紀(jì)90年代走紅的香港女明星的名字。影片的男主角黃覺曾經(jīng)在接受采訪時說,“湯唯只要籠住一個‘蛇蝎女子’神秘氣場,這個角色就能成立。”“蛇蝎女子”是畢贛一開始給湯唯角色時提出的設(shè)定。
而湯唯說,自己在這部電影里所有的表演,其實(shí)就是在詮釋這四個字背后的人物,“我要明白她為什么這么做,為什么要做出一些那么奇怪的神秘的舉止。我是幫導(dǎo)演去解釋。”
這次的表演和以往有不同,人物沒有過于戲劇性的行動線,很多時候表演的是結(jié)果和狀態(tài),但湯唯說自己在演的時候,“我是那個人,有她自己的心事和愿望,還有她的恐懼,每一場都是完完整整的。”這份細(xì)致甚至延續(xù)到她會停下來和導(dǎo)演爭論,當(dāng)時那個房間里的溫度應(yīng)該是多少度?
這樣的討論是不是重要?在這個創(chuàng)作群里,好像很重要。因?yàn)槟抢锏沫h(huán)境氣氛,直接影響到人物的狀態(tài)。第二部電影,他還是選擇在家鄉(xiāng)凱里,《路邊野餐》里有大量的自然景致和日光下風(fēng)土人情,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則是另一個黑漆漆的迷幻凱里。

湯唯提前兩個月開始學(xué)習(xí)貴州話,畢贛的方法很特別,他給她介紹了自己的同學(xué)做語言老師,每天打電話聊天。湯唯在電話里的身份是“搞金融的萬小姐”。同學(xué)一開始一本正經(jīng)地教學(xué),湯唯卻變著法去挖同學(xué)的八卦,扒著生活里的點(diǎn)點(diǎn)滴滴讓對方說。借由貴州話說出的生活過往,讓湯唯開始進(jìn)入遙遠(yuǎn)地區(qū)個體的生活經(jīng)驗(yàn)。
再提前一個月進(jìn)組,在凱里漫無目的游蕩,吃當(dāng)?shù)氐氖澄铮蚴畨K錢一盤的臺球。想象畢贛在這里成長的樣子,一路走到畢贛的外婆家。“那一段時間在凱里,真的是在消磨時光啊。”消磨這種詞,對湯唯這樣的演員來說“太奢侈了”。可是磨著磨著,“好像山里的濕氣混進(jìn)了身體”,這也造就了角色濕漉漉的感覺。濕漉漉的感覺從《路邊野餐》氤氳延續(xù),畢贛的電影依然是一場雨。
#p#分頁標(biāo)題#e#

豪豬:被困的和終將沖破的
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后半段是長達(dá)一個小時的3D長鏡頭。借由鏡頭語言的不同,影片的前后被割裂成兩段。黃覺形容這是鏡子外面和里面相互映照的世界,畢贛的形容則更文藝:一半是記憶,一半是罌粟。
除去這種意向的表達(dá),現(xiàn)實(shí)要完成這樣的長鏡頭,大費(fèi)周章。從山洞出,經(jīng)由蜿蜒山路到索道,索道下行,到達(dá)臺球廳,再下臺階到舞臺的化妝間,畢贛營造這些空間,“層次就像墜入到一層一層的夢境里面。”
搭建場景和試驗(yàn)用掉一年的時間。最初他想實(shí)拍,但機(jī)器太重沒有辦法達(dá)成許多運(yùn)動要求,換了集中器材,最后選擇后期合成。演員的表演需要經(jīng)過精心排練,在長鏡頭中要完成多場戲還有借由有些巧合,比如臺球如果不能一桿進(jìn)洞,整個鏡頭就不能成立。集中拍攝后,畢贛認(rèn)為結(jié)果不理想,幾個月后又重新召集演員“補(bǔ)拍”。
困難是從始至終的,長鏡頭的設(shè)定讓影片制作不斷超支,片頭能夠看到長長的出品名單,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加入的投資。5000萬成本,在文藝片里是個“天文數(shù)字”,何況他還是只拍過一部成本10萬元長片的年輕人。在做預(yù)算階段,畢贛不懂電影工業(yè),并不知道想要的效果究竟需要花掉多少錢。“但是你知道,如果有一些好的反響,就證明那些堅(jiān)持是對的,當(dāng)時如果接受妥協(xié),可能就不會有現(xiàn)在的結(jié)果。”畢贛對自己的堅(jiān)持感到慶幸。
華策影業(yè)董事長傅斌星今年在戛納接受采訪時表示,“這部電影雖然貴,但是你能夠清清楚楚地在電影里看到每一分錢花在哪了。”

所有的不確定性延續(xù)到最后一刻,為了“逼迫”導(dǎo)演,湯唯撒謊告訴導(dǎo)演自己只剩最后一天,如果不完成她也沒法“奉陪”。高壓下的畢贛做了決定,拍完后湯唯才告知,她其實(shí)還給他留了時間。這樣的操作基于對畢贛的了解和尊重,知道他需要被推一把,也尊重和相信他的才華。
時隔一年多再問湯唯,回想片場那么多紛繁復(fù)雜的情況,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?她的回答是“豪豬”。是拍那個長鏡頭里臺球廳場景的附近,旁邊的人家養(yǎng)的一圈豪豬,在每個夜晚會去撞擊柵欄,發(fā)出砰砰砰的聲音。還會掉下又粗又硬的刺,城里長大的湯唯沒見過,還去搜集來玩。“我們一班人,跟豪豬一樣,困在那想,怎么辦哪?那些豪豬就在那‘鐺,鐺,鐺,鐺’的陪我們。”
畢贛說這就是拍電影的過程,“你們都聽不懂這種東西,講出來大家都覺得沒意思,或者說我們描述出來大家都聽不懂,但我們想起的永遠(yuǎn)是那些東西。豪豬,或者別的那些看起來有一點(diǎn)點(diǎn)可愛,稍微帶一點(diǎn)痛感的東西。”

野馬:未曾過去的年輕叛逆
預(yù)售破億的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意味著不再是《路邊野餐》那樣的小打小鬧,也不僅僅只接受文藝青年的檢閱。畢贛這一次要走到大眾面前。“藝術(shù)電影有多大的空間,想要用這部電影來試試看。”這是電影剛拍出來的時候出品方說的話。
“宣傳的同事給我看數(shù)據(jù),說很多都是三四線城市貢獻(xiàn)的票房。我自己就是小城市里走出來的,我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過著怎樣的生活,我的朋友會怎么選擇電影。這部電影像外星人一樣出現(xiàn)在人類的生活里面,我覺得特別有趣。”
畢贛記得《路邊野餐》也曾被質(zhì)疑,“也有人說干嘛要這樣拍電影,那些話到今天都已經(jīng)被忘記了。大家只記得那是一部珍貴的電影。所以我覺得是交給時間。” 他把票房看得挺淡,即便之前為了宣傳電影上綜藝這么不按常理出牌的事,他也只說“這是我的工作。”
#p#分頁標(biāo)題#e#

黃覺說,拍完畢贛的電影,感覺自己很難再接別的戲。極致的創(chuàng)作狀態(tài)太爽快,真的能夠在拍攝過程中感受到導(dǎo)演說的拍電影是“偉大”的事,這樣的機(jī)會在演員的一生中也極為難得。
而湯唯形容跟畢贛拍電影,就像玩游戲一樣,過五關(guān)斬六將,每天都像要打通關(guān)一樣的興奮。
“像我們這樣的演員,拍過那么多的電影,都是比較成熟的制作,不會跑偏。所以我特別感謝他,讓我終于有機(jī)會,做一檔這樣子的事,因?yàn)槲乙恢逼诖軌蛴懈嗟呐R場的未知的體驗(yàn),其實(shí)我喜歡這種感覺。我喜歡那種一起去找,可能云里霧里,一轉(zhuǎn)身又豁然開朗的感覺。”
1989年的畢贛小湯唯10歲,比黃覺小14歲。黃覺把和畢贛在凱里耗著的9個月,看做是自己面對“中年危機(jī)”的一場儀式和一份禮物,湯唯則像是終于找到自己少時想要的那份沖動輕狂。“我發(fā)現(xiàn),自己小時候的叛逆好像至今還沒完全過去,”湯唯這么想著又自嘲說,“好像我這個年齡了不該說這種話。但是年輕的時候,這種東西一直在心里面冒啊冒,一直也沒有地方真的讓我去安放。真的是到了畢贛這里的時候,我會覺得所有東西都對了。他的天馬行空也好,他去找月亮也好,找宇宙也好,在他這兒的空間真的好大好大,這是一個大草原,有時候可以一起high起來跑得飛快;有時候慢了沒跟上,那就在那拔草玩吧。”
畢贛問湯唯:“你是說你是匹野馬嗎?”
好在他有草原。